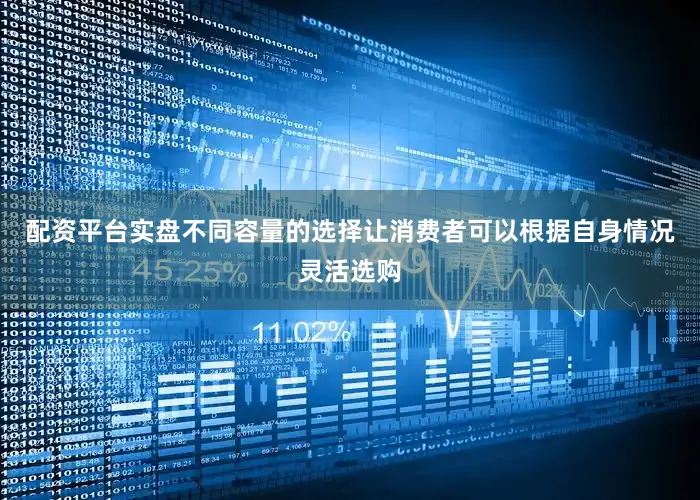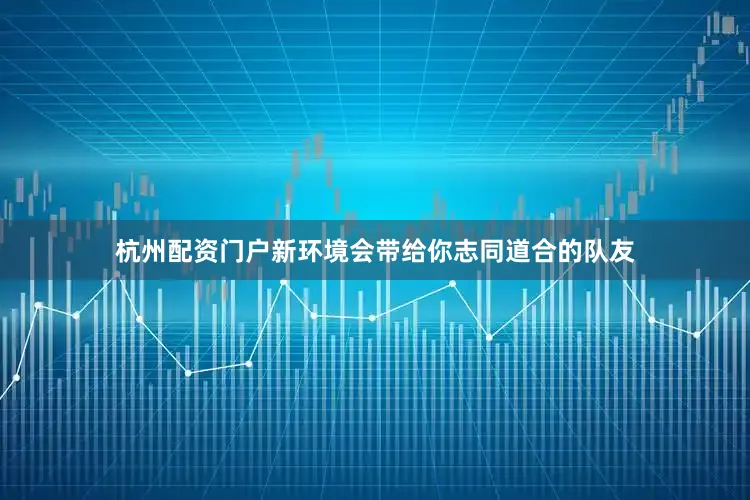□孙晓明 孙辰龙
前期央视热播的电视剧《护宝寻踪》中泰山石敢当的出现,既是民俗文化的具象化表达,也是剧情悬念的载体,其“镇邪”属性与“护宝”主线高度契合。
在中国民间信仰的长河中,泰山石敢当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从汉代《急就章》中的“石敢当”三字,到如今遍布全球华人社区的镇宅石碑;从简单的灵石崇拜,到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泰山石敢当的演变史,恰如一部浓缩的中华民俗文化发展史。本文将带您探寻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起源、演变与传播,揭示它如何从泰山一隅走向世界,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“平安文化”的重要象征。
泰山石敢当是怎么来的
泰山石敢当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的灵石崇拜传统,具有石敢当功能的灵石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的《淮南万毕术》“丸石于宅四隅,则鬼能无殃也”。“石敢当”的称呼最早见于西汉史游《急就章》:“师猛虎,石敢当;所不侵,龙未央”。唐代颜师古注解说:“敢当,所向无敌也。”此时的“石敢当”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修辞,尚未与泰山或具体人物产生关联。
展开剩余84%早期的文献中,出现的都是石敢当,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泰山石敢当。宋真宗泰山封禅后,将泰山神晋号为帝,促使民间对泰山的崇拜不断升温。随着东岳庙在元代的广泛分布,作为五岳之尊的泰山与原有的石敢当习俗逐渐融合,形成了“泰山石敢当”的新形态。”《博物志》称泰山为“天孙,言为天帝孙也”,具有“知人生命之长短”的神力,这种对泰山的尊崇为石敢当信仰注入了更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石敢当与泰山的结合始于宋代。最早的“泰山石敢当”文物是金代皇统六年的泰山石敢当拓片,相当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。2016年,在泰山附近发现了元代泰山石敢当碑石,高70cm,宽41.5cm,厚11cm。碑阳正中为楷书“泰山石敢当”五字,左下角之文为“(大)元延祐五年岁次戊午吉日”。泰山文化学者周郢教授在《新见元延祐“泰山石敢当”碑铭考》中研究认为,这一发现不仅可证实“泰山石敢当”风俗出现时间在宋元之际,同时也可据以推知其发祥地应在泰山附近。泰山信仰中逐步形成的通天、求仙、长生不老、主生死、治鬼、地狱、平安吉祥、有求必应等文化内涵与石敢当的驱邪、镇鬼、压殃、逢凶化吉、有求必应、平安吉祥等观念融合在一起,“泰山石敢当”称号的出现,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,也是泰山信仰和石敢当习俗发展的大势所趋。
关于石敢当的人格化起源,学界存在有趣的争议。太原学者认为“石敢当”源自五代时期太原猛将石敢。《旧五代史·汉本纪》记载:“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锤侍高祖,以处变。”这位勇救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将军因名字与“石敢当”相似,在民间传说中合二为一。太原附近的太山(非泰山)也被认为是“太山石敢当”的真正来源,因史料中多有“太山”而非“泰山”的记载。对此,周郢教授认为:“石敢将军其人,据《姓源珠玑》等书所载,确为五代时太原勇士,但这仅说明历史人物‘石敢’的形象被后世附会到泰山石敢当信仰中,成为其人格化的来源之一。”
唐代(如大历福建碑刻)及宋代(如莆田桥铭)的早期石敢当实物均不带“泰山”二字,其根本功能一直在于镇煞辟邪。“泰山”前缀实为宋代之后添加。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,是泰山在传统文化中作为“群山之祖”和“幽冥主宰”(汉代纬书称“泰山治鬼”)的至高权威地位深入人心。为了赋予石敢当更强的神力,民间将其与泰山这一最负盛名的权威象征结合,最终定型为“泰山石敢当”。这一演变揭示出其本质:它是民间信仰为追求更强效力而主动吸附权威符号的过程,而非起源于泰山本土的传统。
明代以后,石敢当的形象进一步丰富。徐勃《徐氏笔精》中有一首诗云:“甲胄当年一武臣,镇安天下护居民。捍冲道路三岔口,埋没泥涂百战身。”将泰山石敢当作为武将称颂。在山东泰安地区,石敢当则被传说为泰山脚下的一位青年石匠,体魄强健,武艺高强,行侠仗义,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。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的桥沟村被认为是传说中石敢当的祖籍地,村内民宅上至今到处可见“泰山石敢当”碑刻。
从无名灵石到人格化的英雄,从单纯的镇宅功能到多元的文化象征,泰山石敢当的演变历程折射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创造性与包容性。正如学者所言:“在历经千百年演变后,石敢当已经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石敢当与泰山也再难以分离。”
传奇故事与多元形象
在泰安民间,流传着一个关于石敢当驱妖的经典故事。传说泰山脚下住着一个叫石敢当的青年,为人勇敢正义,好打抱不平。大汶口镇一户张姓人家的女儿被妖气缠身,每到黄昏便有妖风从东南方袭来,使姑娘面黄肌瘦,奄奄一息。张家父母慕名请来石敢当相助,他准备了十二童男、十二童女,男孩持鼓,女孩拿锣,还有一盆香油和粗灯捻。天黑后,石敢当点燃油灯并用锅扣住,静待妖怪。当妖风袭来时,他猛地踢翻锅,灯光大亮,童男童女齐声敲锣打鼓,吓得妖怪仓皇南逃。
这个妖怪后来流窜到福建继续作恶,当地人又将石敢当请去。面对妖怪的四处流窜,石敢当想出一个妙计:“泰山石头很多,我找石匠打上我的家乡和名字——‘泰山石敢当’,谁家闹妖气,就把它放在谁家的墙上,那妖就跑了。”从此,刻有“泰山石敢当”的石碑便成为民间镇宅辟邪的吉祥宝物,这一习俗流传至今。
在广东徐闻县,则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传说。康熙年间,该地几任知县到任数日便离奇死亡。一位黄姓知县携风水先生赴任,发现县衙正对一座宝塔的影子,前几任县官皆因无法承受宝塔的压力而亡。风水先生命人在县衙门前立“泰山石敢当”石碑,以泰山之神力抵御宝塔阴影,此后黄知县平安无事。这个故事展现了石敢当信仰在风水学中的应用,也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应对智慧。
随着时间推移,石敢当的形象不断演化丰富。明清时期,石敢当从“石将军”演变为“石大夫”,功能也从单纯的镇宅驱邪扩展到治病救人。立于泰安市岱岳区祝山的《石大夫庙叙》碑刻,详细记述了石敢当从镇邪灵石到治病医士的形象演化轨迹。在山东莱芜一带,石敢当甚至被视为可治百病的“石大夫”,民众向其祈求安康。这种功能的扩展使石敢当信仰更具人间烟火气,增强了其生命力与影响力。
特别有意思地是,石敢当还与姜太公、黄帝等历史神话人物发生了关系。民间传说姜太公封神时竟忘记了自己,最后自封为“泰山石敢当”。另有故事讲述黄帝与蚩尤大战时,蚩尤登上泰山挑衅:“天下有谁敢挡(当)?”女娲投下泰山石喝道:“泰山石敢挡(当)!”助黄帝战胜蚩尤。这些附会虽然缺乏历史依据,却丰富了石敢当的文化内涵,使其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叙事联系起来。
从这些多元的民间叙事中,足以看到石敢当形象的共同特质:勇敢正义、保护弱者、智慧应对邪恶。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平安吉祥的心理需求,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想。正如专家所言:“泰山石敢当所表现的‘吉祥平安文化’体现了人们普遍渴求平安祥和的心理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创造力。”
从泰山到世界的文化使者
泰山石敢当的传播堪称一部微缩的中华文化外传史。有人称其为“泰山的驻外使节”,其传播范围之广,在民俗信仰中独树一帜。这一过程以泰山为中心,先广涉齐鲁大地,再以山东和福建为两大集结地,辐射全国乃至海外。在山东,几乎村村户户都有石敢当,尤其是“石将军”等人物造型的泰山石敢当,成为地域特色。泰安市岱岳区的桥沟村、济南朱家峪村等地,至今保留着丰富的石敢当文化遗存,章丘北邓家村还建有香火不断的石大夫庙。
福建在石敢当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早在唐代,福建汉民就将“石敢当”作为镇宅风水器物,闽南的厦门、泉州、漳州成为信仰最集中的地区,并由此传播至海外。明代,随着福建人下南洋,泰山石敢当文化被带到东南亚各地。葡萄牙统治时期的澳门曾发行石敢当庙邮票,上世纪70年代香港拍摄过以石敢当为题材电影。
在日本,石敢当不仅出现早,而且广为传播,经久不衰。从最南部的冲绳,九州的鹿儿岛、熊本、佐贺,四国的德岛,到本州的滋贺、东京、宫城、秋田,甚至最北端的北海道函馆市,都发现了泰山石敢当的踪迹。在东南亚的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缅甸、越南、老挝等国家,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,几乎都能找到石敢当的身影。欧洲、澳洲、美洲的唐人街也不例外,石敢当已成为海外华人保持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。
特别有趣的是,石敢当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时,往往与当地文化融合,形成新的形态。四川省汶川县的石敢当上端多雕有羌族兽头图腾;阿坝州的九寨沟有泰山石敢当标志性雕塑。这种本土化使石敢当信仰在不同文化中都能找到生存土壤,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。
从汉代灵石到当代处处可见的泰山石敢当,从泰山一隅到全球华人社区,泰山石敢当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。它由简入繁,由实入虚,由物质入精神,最终成为一种文化基因,它所体现的“吉祥平安文化”反映了人类对和谐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,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。在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新的双轮驱动下,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,这颗民俗文化的明珠必将绽放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,继续讲述属于中国人乃至地球人的平安故事。
栏目策划/编辑 马纯潇
发布于:山东省钱龙配资-配资门户网-南宁股票配资-股票的杠杆交易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